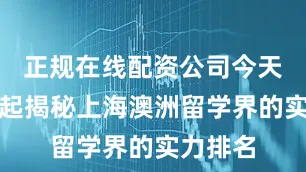同治十三年,即公元1875年一月十二日,年仅亲政一年的同治帝载淳在紫禁城的养心殿不幸驾崩,享年十九岁,被追尊为穆宗。
鉴于同治帝膝下无子,继承皇位的难题便成为了慈禧太后亟待解决的首要政务。

依照大清祖宗家法,子承父业,若大行皇帝膝下无子,便需从其亲侄子中择一人继位。然而,同治帝既无亲兄弟,亦无亲侄,依照祖制,此时便需从道光帝的曾孙之中,即咸丰帝兄弟之孙辈中,寻觅合适的帝位继承人。
当时,有人选吗?
血统不理想。
咸丰帝的子孙均以“溥”字为辈分,而在同治帝不幸离世之际,溥字辈中仅存咸丰帝长兄奕纬的孙子溥伦一人。然而,溥伦并非奕纬的亲生孙儿。由于奕纬未曾有子嗣,溥伦便从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一脉中过继而来,实则成为了永瑆的直系孙辈。由此,溥伦与咸丰帝的血缘关系相隔甚远,难以称得上是理想的继承人选。
慈禧太后对此颇为看重,其情理之中,咸丰帝乃是其丈夫,自然不愿将皇位传予血统较为疏远的旁系宗亲。然而,若考虑到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,溥伦的血统疏远不过是她借口之一。可以断言,即便溥伦的血统并无瑕疵,慈禧太后为了维持垂帘听政,掌握朝政大权,恐怕也不会倾向于选择溥字辈的人选。
显而易见,这一层微妙的关系,即便是朝堂之上的智者亦能洞察一二,然而他们虽心知肚明,却因种种顾虑而未敢直言。
未直言相斥,实则暗流涌动,怀有抵触与反对之情。实际上,朝中大臣普遍持有类似见解。慈禧太后拒不选取溥字辈,公然违背了祖宗定下的规矩,意在谋求更大的皇权。
然而,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已久,凭借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,她果断地确定了帝位继承的人选,目标直指咸丰帝的亲侄子,即载字辈的皇族成员。
当时人选都有谁?
一共三人。
两位分别是恭亲王奕䜣的嗣子,一位年方十八的载澂,另一位则是十一岁的载滢;而另一位则是醇亲王奕譞之子,年仅四岁的载湉。
面对这一“三选其一”的抉择,慈禧太后尽显其权欲之重与私心之深。
拥有英明的君主乃国家之幸,据此推论,十八岁的载澂理应成为三人中的最佳人选。然而,在慈禧太后的眼中,最初被淘汰的却是载澂。
提及载澂,慈禧太后对他恨之入骨。在她眼中,正是这个载澂导致了她儿子的不幸,若非载澂的引诱与指引,她的儿子绝不可能擅自逃离皇宫,沉迷于花街柳巷,染上种种污病;若非染上这些污病,即便儿子不幸感染天花,也不至于无药可救,最终撒手人寰。如此深仇大恨,慈禧太后岂能轻易置之不理?纵然她为了江山社稷可以放下个人恩怨,却也绝不可能将大清的皇位托付给这样一个行为不检、品行恶劣之人。
此外,十八岁的载澂身为恭亲王之子。在慈禧看来,恭亲王始终是她掌握皇权的重大隐患。若将皇位托付给已至亲政之年的载澂,父子二人一旦联手,稳固皇位,掌控朝政,不仅会使她愧对昔日与恭亲王共同为争夺皇位所付出的辛劳,咸丰皇帝,而且她继续垂帘听政的愿望也将化为泡影。
审视十一岁的载滢,理同此说。何况他容貌丑陋,药物长期不离身,显而易见,他似乎是个软弱无力的废物。

醇亲王奕譞之子,年仅四岁的载湉,情形自是迥异。
载湉,不过四岁稚龄,一旦立为储君,慈禧太后便得以悠然垂帘听政长达十四载,随心所欲地塑造其性格与才能。即便载湉成年亲政,本质上仍不过是受制于她的木偶。再者,醇亲王与恭亲王性格迥异。自辛酉政变以来,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关系,表面上是共同分食皇权之利,实则暗流涌动,争夺皇权之权。相较之下,醇亲王乃慈禧太后精心栽培,用以抗衡恭亲王之选。二人之间,本质上犹如主仆。慈禧太后向醇亲王索求忠诚,自是信心满满,有绝对的把握。
最终一点,亦为关键所在,醇亲王的福晋,即载湉生母,乃慈禧太后的亲妹妹,而载湉则是她的亲侄子。这份血缘之亲无人能出其右,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
因此,慈禧太后选定“载”字辈,表面上看似是出于无奈,实则自始至终,她的目光始终聚焦于这一明确的方向。

然而,在那个时局,要将这头等大事稳妥推进,慈禧太后亦不得不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难题。
慈禧执掌朝政,其卓越之处在于她极其擅长运用平衡之术。
坚定地立下将载湉载入史册的决心后,慈禧太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平息皇族内部的种种非议、不满、嫉妒,乃至愤怒情绪。
慈禧太后之压制化解手段,宛如无迹可寻,高明至极。她与醇亲王默契合作,一连编排了多出令后世津津乐道的宫廷佳戏。
揭晓谜底的那日,醇亲王偕同几位宗室亲王及军机大臣一同入宫,虔诚跪听两宫太后颁布对嗣君的圣旨。
醇亲王的风采格外引人注目,当他得知儿子获选的消息后,悲痛欲绝,竟至痛哭失声,随即晕厥倒地。待他苏醒过来,那份哀戚依然未曾消散,醇亲王屡次三番地哀求两宫太后撤销之前的决定,那情状之悲切,直教人感同身受,心生怜悯。
这乃是一场戏,慈禧太后自是断然不会应允醇亲王的恳求。
恳请朝廷赐予卸任所有职务,以空置爵位,以彰显对天地之间虚位以待的尊崇;同时,亦是为宣宗成皇帝保留一位愚钝无才的子孙。
此举旨在封堵恭亲王一众的言辞,慈禧太后遂即点了头,同意了这一提议。
尚未落幕,第三日,醇亲王再度进言,提议仅保留一空爵位,自此往后,永不增设任何新衔。为防范未来有人妄图侥幸攀附,特此存档此疏,以作信物。
此言一半源自醇亲王之肺腑,旨在平息慈禧太后的猜疑之心,明确表达即使身为新帝之尊亲,亦绝无勃勃野心;另一半则传达了慈禧太后之意,旨在消弭朝堂之上纷扰之声。

恭亲王奕䜣对载湉之选而非己子,内心实则充满不悦。朝中大臣亦对慈禧太后此一违背祖训之举多所非议。然而,鉴于慈禧太后之强势,醇亲王那近乎卑微的表演,实在令人难以开口。恭亲王亦然,无人敢于公然表达异议,唯有默默接受这一现实。
此成就既至,载湉继位的障碍已基本扫除,然而,慈禧太后所须应对的棘手问题,远未告终。
难题还有什么?
既已确立载湉为同辈,而治理朝政长达十余载的同治帝却无子嗣。作为已故皇帝的亲生母亲,慈禧太后,您理应提出一个能够让朝中大臣们信服并接受的解释。
难办,慈禧狡猾。
她试图用一个含糊其辞的表述来搪塞这个问题。
同治帝崩逝之际,慈禧太后以两宫皇太后之名义,颁发了一道懿旨:“载湉嗣位文宗显皇帝,继任皇位,待嗣皇帝诞育皇子,即令其承继先帝为嗣。”
一经颁布这道圣旨,慈禧太后即刻不容稍缓,随即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。
如此,载湉登上了光绪帝的宝座,而大清王朝延续两百余年、世代相传的“子承父业”的爱新觉罗家法,亦随之在这位叶赫那拉氏女性手中宣告终结。
数年间,表面上看,君臣之间相安无事,然而实际上,慈禧的这番说辞并未能真正蒙蔽过旁人。
朝中官员私下纷纷热议,太后的圣旨提及,待新皇帝诞下子嗣便接续先帝的皇位,这究竟意味着何事?
若仅论继承血脉,那便如同仅承续香火,而未能接续江山。先帝的神位将来自当安置于太庙之中。太庙祭祖乃天子独享的尊荣,旁人无权涉足。如此一来,若先帝的神位无人祭祀,那所谓的继承又岂非徒有虚名!如此情形,太后又怎能面对列祖列宗,以及那命途多舛的亲生之子。
若继承即等同于承袭皇位,则此说亦谬矣,实则触碰了大清朝的忌讳所在。
此话怎讲呢?
若嗣位等同于继统,那么今后皇上的长子,即先帝大行皇帝的子嗣,亦即太子,岂不是公然违背了圣祖康熙皇帝既定,后世未曾有悖的国策——不预先立定太子?
继嗣之事,若非继承帝统,则显得不合理;而若不继承帝统,亦是错谬。慈禧太后在权谋纷争中直至终老,竟不慎陷入自己设下的无解困境。
这是把柄呀。

光绪五年,事出。
五月,穆宗同治帝的陵寝工程宣告完工,朝廷计划举办一场盛大的穆宗梓棺永安大典。彼时,吏部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主事,名为吴可读。按照官职品级,主事仅是六品的小官,理应无权出席奉安大典。然而,吴可读却屡屡恳求,鉴于其忠孝之心难得,朝廷最终破例应允,特许他参与此次大典。
不料,典礼既毕,归京途中,吴可读竟怀抱遗折,于破败的庙宇中自缢而亡。
吴可读遗折主要内容为何?
当时,穆宗驾崩之际,太后下达的懿旨中仅提及了嗣位的安排,并未涉及皇位的传承。回顾历史,曾有过嗣位却未传承皇位的恶劣先例,其后果是令人痛心的。由于担心皇位旁落,恳请太后即刻为穆宗指定继承者,并明确指出此继承者即为未来的君主。今后,即便皇帝有一百个皇子,亦不得觊觎皇位。
这便是光绪朝初期广为人知的“吴可读尸谏太后”一桩大事。
初见之下,吴可读以生命为代价,陈词恳切,期盼穆宗能够留下子嗣,世代承袭皇位,堪称大清难得的忠臣孝子。然而,若仔细推敲他的遗折,其中亦不乏疑点。首先,他公然以生命相谏,似乎在担忧朝堂秩序的稳定,此行为颇有沽名钓誉之嫌;其次,他通过以死相逼的方式,迫使慈禧太后立刻为穆宗立嗣,若深入思考,他或许只是他人手中的棋子。
缘由显而易见,那时的光绪皇帝尚且年幼,与生育子嗣相距甚远。吴可读却偏要在此时为穆宗选定继承人,若慈禧太后在无奈之下应允,也只能在近支王公中寻觅溥字辈的人物。
当时近支王公有溥字辈人选吗?
还真有,而且是唯一。
两年前,恭亲王的长子载澂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子嗣,取名载倬。
原来真相大白,吴可读挺身而出,依据祖传家规,竭力劝谏慈禧太后,实则其背后动机,乃是为恭亲王的嫡传孙子争取帝位之机。
慈禧太后的洞察力堪称犀利,自是能洞悉其中的玄机,然而即便如此,又岂能轻易脱身?吴可读倚仗着祖宗家法以及朝堂道义的至高点,若此困境无法破解,慈禧太后不仅将面临朝中清流的质询,更会在将来不断被人拿捏,成为无休止的把柄。
协办大学士徐桐、刑部尚书潘祖荫、工部尚书翁同龢均力图协助慈禧太后解决这一棘手难题,然而,这些权贵人物却仅仅局限于对吴可读此举的不合时宜进行指责,认为其不应无故引发纷争,却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。

慈禧太后未曾预料到,正当她陷入困境之际,朝廷中地位微不足道的张之洞竟然递交了一篇堪称绝妙的“救驾”奏折。
登台伊始,张之洞便以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胆识,对五年前慈禧太后下达的懿旨进行了深入阐释:世人皆言太后只立嗣而不立统,实乃你们未能领悟圣意。今我代太后告知诸位,立嗣之举即意味着立统。
基于这一前提,吴可读所提及的穆宗大统旁落之论,无疑是毫无根据的妄言。再则,穆宗的子孙正是现今皇帝的亲生骨肉,天下间岂有父亲伤害自己亲生儿子的道理?因此,吴可读所述为争夺皇权而引发的残杀,纯属子虚乌有。至于他提出的应预先指定一位既继承宗嗣又掌握皇统的建议,这既违背了祖宗的家法,又显得居心叵测,太后理所当然应当予以严词驳回。
张之洞深知将面临质询,于是他反问:“既然您认为立嗣便是确立统治,那么请问,若与康熙帝未预立太子的政策相悖,又将作何解释?”
张之洞回答得极妙。【转换失败】:今上日后必定皇子众多,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,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。此则本乎圣意合乎家法,而皇上处亦不至于碍难。
什么是上智?
这是典型。
慈禧太后阅罢张之洞所呈奏折,不禁赞叹连连。
张之洞仅以数语,便将吴可读所提难题剖析得淋漓尽致。他不仅深谙我心里的困顿,更能将我欲言而难尽的道理阐述得明明白白,更是将棘手的问题圆满解决。在满朝文武百官中,如此人才实属罕见,他无愧于探花郎的美誉。
启远网配资-配资杠杆平台-配资炒股网官网-线上实盘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