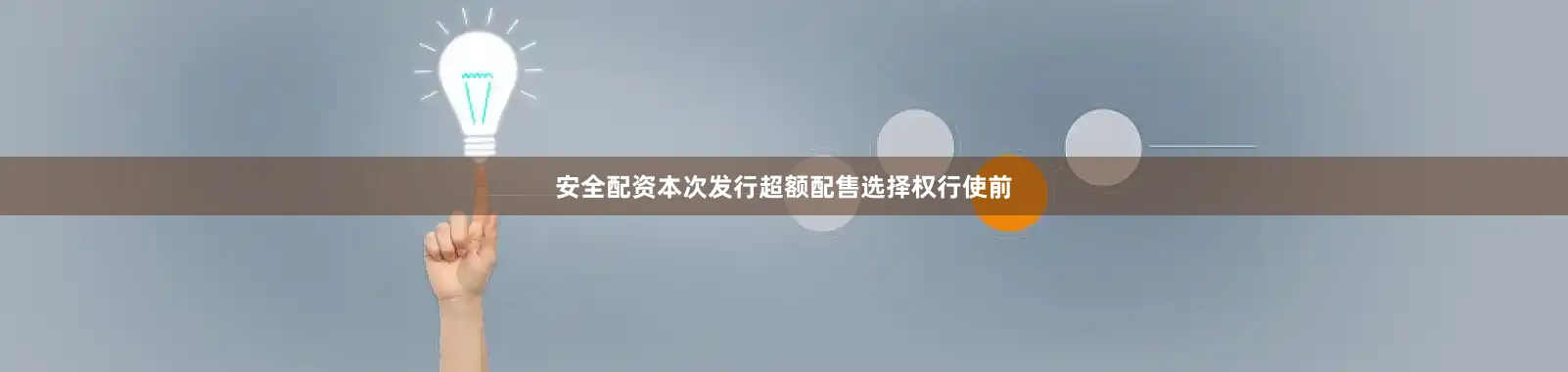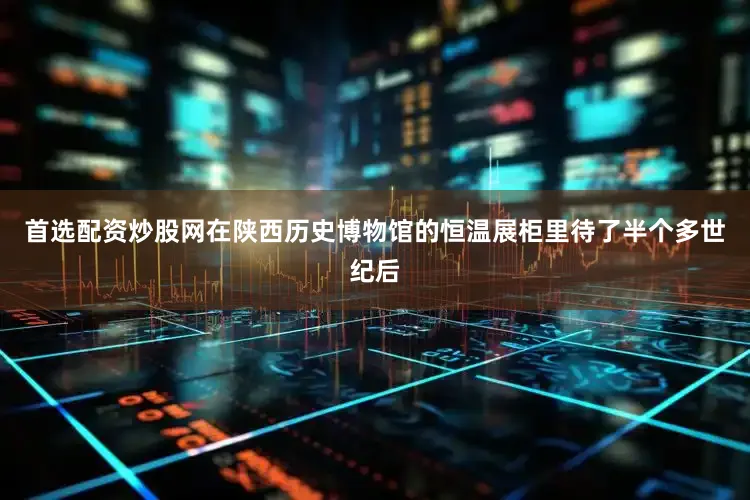
我腹身的饕餮纹,是三千年前铸工一凿一錾刻下的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恒温展柜里待了半个多世纪后,他们说要带我去江南“做客”。出发前三天,穿白大褂的李老师就天天来跟我“打招呼”,用软布擦去我足根的微尘:“老伙计,路上得委屈几天。”我那时还不懂,这趟“出差”,要过多少道关。
第一道关:被裹成“棉团”的体面
离开展柜那天,库房的灯比往常亮三倍。两个戴无粉手套的年轻人蹲在我面前,动作轻得像怕惊醒睡着的猫。他们先给我套了件“无酸纸外衣”,纸是软的,顺着我腹身的弧度贴上来,连饕餮纹的齿缝都没被硌着。接着,我的三只足被分别塞进定制的海绵套里——那海绵上有和我足形一模一样的凹槽,像是给我做了双“软鞋”。
展开剩余80%“抬的时候注意重心,它肚子沉。”李老师在旁边盯着,声音压得很低。我被轻轻托起,放进一个木框里。框子内壁铺着一层绒布,外面又裹了三层防震棉,最后盖上带透气孔的盖子。透过孔隙,我看见战国的铜剑被装在另一个箱子里,剑鞘上的绿松石闪了闪,像是在说“一路顺风”。
后来才知道,这叫“二次包装”。李老师说,硬木框防挤压,海绵吸震动,无酸纸隔潮气——我们青铜器虽硬,却怕潮怕磕,这层层包裹,是给我们留足体面的“铠甲”。
第二道关:卡车里的“恒温小天地”
我被抬进一辆白色的卡车。车厢里没有方向盘,只有一排排金属架,冷气丝丝往外冒。李老师拿着个小仪器贴在我箱子上,屏幕上跳出“18℃,55%”的数字,他点点头:“湿度稳了。”
卡车启动时,我没感觉到往常坐货车的颠簸。后来听跟车的王师傅说,这车的减震系统是特制的,减震是通过气垫悬浮功能实现,连司机换挡都要比普通货车慢半拍。“你们这些老物件,得像伺候老寿星似的。”他拍了拍我箱子的侧面,声音透过棉层传进来,闷闷的。
走山路时,车厢突然轻微晃了一下。王师傅立刻停下车,打开厢门检查。他用手摸了摸固定我箱子的皮带,又看了看防震棉的松紧,折腾了十分钟才重新上路。“刚才有块石头,怕震着你。”他像是在跟我解释,又像是在跟自己较劲。
第三道关:高铁上的“静音包厢”
到了中转站,我被移进一个银色的集装箱。这里比卡车车厢更安静,只有仪器运行的“嗡嗡”声。王师傅说,这是高铁的“文物专箱”,温度湿度和卡车里一模一样,连震动幅度都控制在“一片叶子落地”的力度。
高铁开动时,我听见外面传来“呜”的长鸣,比卡车的声音清亮多了。透过集装箱的观察窗,我看见云在往后跑,跑得比博物馆院子里的鸽子还快。王师傅隔着玻璃冲我比划,手里举着个小本子,上面记着“10:30,湿度54%”——他每隔半小时就要记一次数据。
中途停站时,有人来检查集装箱的锁扣。他们戴着白手套,动作轻得像拆信封。我听见他们说:“这鼎可是宝贝,当年周武王赏给功臣的,路上不能出半点岔子。”原来他们都知道我身上的故事,知道腹底那行模糊的铭文里,藏着三千年前的赏赐与荣光。
最后一程:展厅里的“亮相”
抵达江南的博物馆时,天已经擦黑了。他们没立刻把我搬进展厅,而是让集装箱在馆外“晾”了半小时。王师傅说,这是让我慢慢适应这里的空气,“就像人换地方要先缓缓”。
进展厅的那一刻,我听见了“嘶”的抽气声。灯光慢慢亮起来,照在我被擦得锃亮的腹身上,饕餮纹的每一道纹路都清晰得像刚刻好的。有个戴眼镜的老先生凑过来看,手指悬在我足边,半天没敢碰:“运输得真好,连足根的老包浆都没蹭掉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为了让我顺顺利利“出差”,他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模拟路线,算好了晴天雨天,测遍了山路平原的震动频率,连包装的棉层厚度都改了七次。
现在我站在江南的展柜里,每天看着穿旗袍的姑娘、背书包的孩子在我面前驻足。他们说,我身上的饕餮纹,是跨越千里的“信使”。可我知道,真正的信使,是那些在运输路上为我裹棉、测温、停下车检查防震带的人——是他们,让三千年前的青铜,能稳稳地走到今天的阳光下。
发布于:山东省启远网配资-配资杠杆平台-配资炒股网官网-线上实盘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交易能在肛肠黏膜高效形成智能保护膜
- 下一篇:带杠杆的股票报42849.67点